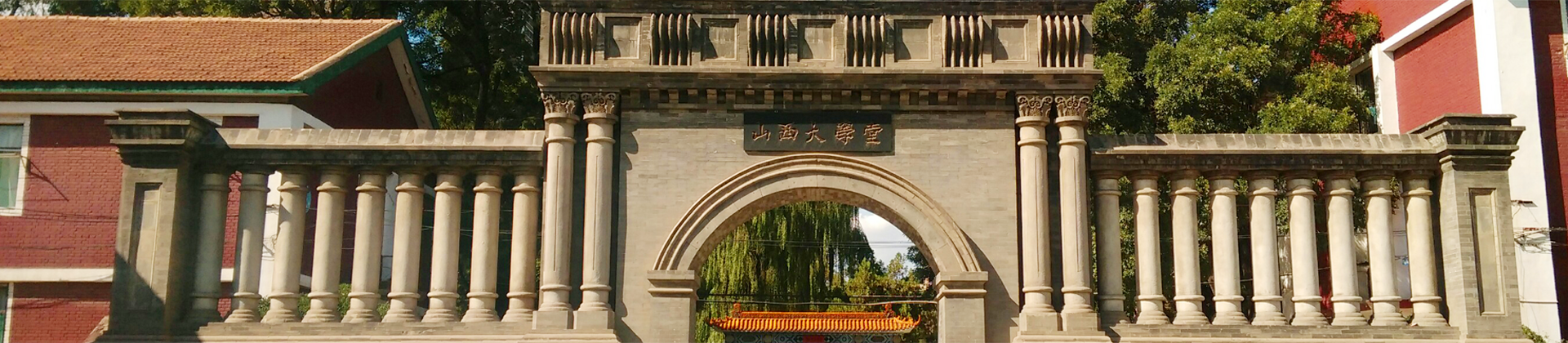
董华锋,山西昔阳人,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四川佛教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,入选四川省天府青城计划,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、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委会委员、四川省考古学会石窟考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,主要从事佛教考古、敦煌学、出土碑刻等方面的教学、研究工作。出版著作4部,发表论文60余篇。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、四川省教学成果一等奖、二等奖、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奖励。

川渝地区是中国石窟的重要分布区域。根据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的数据,四川省共有石窟(含摩崖造像)2134处,重庆市716处,两省市石窟数量占全国的47.6%。这些石窟零散分布在川渝各地,开凿时间从北朝延续至清代,造像内容兼涉佛儒道三教,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,同时,石窟周边往往会保存有墓葬、古道、堡寨、盐井等关联遗存。
在川渝石窟的众多研究问题中,营造程序是一个重要的论题,是深入认识石窟寺这类考古遗存的重要切入点。董华锋教授的专题报告《川渝石窟的营建程序》着重从四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读:
一是川渝石窟的供养人。功德主出资供养是石窟营建的首要程序。有关川渝石窟的功德主,过去关注较多的是个人或家庭,但实际上,民间结社也是一种重要形式。川渝石窟中保存的古代民间结社资料信息十分细碎,难知其全貌,但若参照敦煌等区域同类问题研究已经形成的认知,我们即可连缀成一个相对系统的整体认识,从而大体理清川渝石窟古代民间结社的流行时间、组织结构及其发展演变轨迹。
二是川渝石窟的工匠团队。石窟的营建离不开专业的工匠团队。唐宋时期,川渝地区形成了分工完备、级别分明、组织得当的石窟工匠体系。在这一体系中,工匠之间有工种区分,有技术级别差异,还拥有得力的组织人员;他们各司其职,是石窟的直接营造者,是该区域得以大规模开凿石窟的专业技术人员保障。
三是川渝石窟的营建仪轨。川渝地区的石窟雕绘完成后一般都会举行配套的仪轨——庆赞斋会。这是石窟营建程序中的重要环节。这一环节具有很强的仪式性,保存下来的实物遗存较少。从石窟中有限的铭刻资料来看,石窟营建中的斋会种类众多,斋会的规模大小不等,斋日的择选也有多种方式。这一环节是一次石窟营建活动真正完成的标志。
四是川渝石窟的后期重妆。石窟建成后,随着时间的推移,造像会因自然或人为等原因脱彩、残断甚至坍塌,故有后期的各类修妆活动。重妆是石窟营建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行为。历史上形成的后期重妆遗存是石窟寺文化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后期重妆原因众多,功德主的身份多元,方式各异,目的同样是施造功德,且完成后还会再次举行庆赞斋会。重妆不仅使脱彩的龛像“普焕神容”,同时也使石窟寺的文化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不断拓展。
报告最后,董华锋教授总结道:石窟寺是一种内涵复杂的考古遗存。对于这类考古遗存的研究,不仅涉及田野考古、分期排年、题材信仰、样式风格、历史背景、文化交流等问题,还应关注营建程序的问题。总的来看,川渝石窟经历了漫长的的营建历程,某种意义上讲,这一历程甚至一直延续至今。供养发愿、营建工匠、庆赞斋会、后期重妆是目前关注相对较少的几个环节。透过石窟及附着其上的铭刻材料,可以大体厘清川渝石窟的营建程序。



